一,
走进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前厅,第一眼就会看到那座近30米高的巨型骨架模型——一头成年重龙好像马戏团的大象,用后腿直立,高悬的前肢,准备凌空下击。一只幼崽瑟缩在它身后。在它们面前,是一头凌牙厉爪的特异龙,咄咄进逼。

重龙是我们星球上行走过的最大动物之一。成年个体身长达26米,体重约20吨。这种生活在侏罗纪晚期(1亿4千5百万年前)的素食动物,属于四足行走的蜥足类恐龙。而伺机进攻的特异龙,则是那个地质年代最大的肉食动物,处于食物链的顶端,就像今天非洲草原上的狮子。
自从1991安装完毕,这件装置已成为纽约重要的公共艺术,壮观并充满戏剧性张力。总之,酷。一个史前动物界的生存竞争场景,被呈现为善恶决战之前,张弓待发的瞬间。有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说科学是一种话语构建。至少在古脊椎动物领域,这话倒不完全像是诡辩。由此也不难看出,对于当代博物馆,教育和娱乐之间的功能划分,已不再泾渭分明。
争议也随之而来。比如特异龙是否会单独挑战成年重龙?它们的体重相差近20吨。就像再悍猛的越野车,你也不敢开着它擦撞满载的集装箱货车。更多疑问,则集中在重龙身上:蜥足类恐龙能用后腿直立吗?对于雄性个体,前肢离地是起码的要求,否则无法交配。然而达到几乎垂直的程度,就意味着心脏要把血液泵送至20多米的高度,为脑部供氧。甚至有专家推测,重龙可能长了八个心脏,沿着长颈,将血液分级压升到高耸的头部。
事过20年,当初参与装置设计的马克·诺雷尔,以一种特别的方式,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诺雷尔在博物馆主持古生物学部门。由他策划的新展览“世界最大的恐龙”,是这个月纽约人议论最多的文化事件之一。很多人认为美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。但我个人有个粗浅的观感,即他们的知识分子经常不弄文科,而是一些从事普及工作的科学家,努力激发公众的智力好奇心。这种普及不是专业水准的降低,而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文明秩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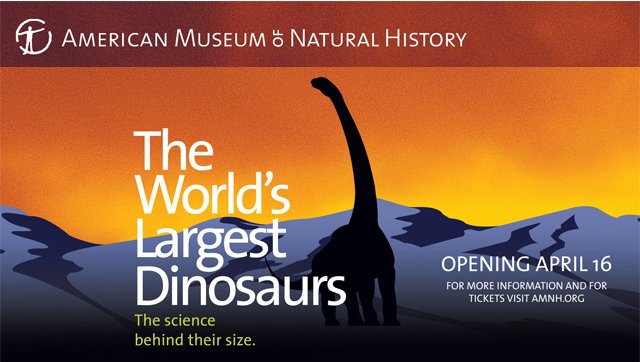
新展设在博物馆四楼。进入特设的展室之前,不妨先去转转隔壁的恐龙大厅,做为地球现任统治者的一员,检阅一下这个自然史上最成功的陆生动物。如今它们只是摆成各种姿势的石头,比宠物更安全,哪怕凶恶的霸王龙和恐手龙,还有那只装模作样,啃食猎物骨头的特异龙。
这里收藏的早期恐龙不多,最有名的标本,是一具基本完整的恩氏宽街龙,来自三叠纪,距今两亿年前后。它以植物为食,属于蜥足类的原始形态。此后几千万年,那个支系繁育出空前绝后的庞然大物,也就是“世界最大的恐龙”中的主角。那时地球已经进入侏罗纪。在这个新的地质时代,原本合而为一的盘古大陆逐渐分裂,型成北方的劳亚大陆和南方的贡瓦纳大陆。当时的气候普遍温暖湿润,地表覆盖着繁茂的蕨类和裸子针叶植物。
这间展厅很大一部分,被一具拱桥般的骨架化石占据。那是迷惑龙,可以代表蜥足类的一般特征——笨重而庞大,伸着长脖子,拖着长尾巴,就像恐龙片中总会看到的那些大家伙一样。要论体量,就算前面提到的重龙,也不能和它相提并论。侏罗纪是它们的生活的黄金时代。有时候我甚至怀疑,那个时代的地球引力,是否要比现在小很多。
每次走过这些巨大的化石,我都会心生敬畏。自三叠纪晚期,到白垩纪结束时骤然灭绝,这些家伙在陆地上统治了一亿六千万年。相形之下,包括我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,除物种多样性之外,并不特别成功。就像文明史范围之内,当我们面对汉唐、罗马、阿拉伯,那些以往帝国的成就,也常会自叹不如。
曾《纽约时报》上见过一篇文章,说很多小孩喜欢恐龙,是因为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大人不懂的怪词,组成一套他们自己的黑话,而古怪的原因,又随各国语言变化而异。
侏罗纪就属于这种怪词。它的最初来源是大科学家洪堡发现,汝拉山脉的瑞士部分裸露的的沉积岩层,与和相邻地层时代迥异。后来则由法国人布隆尼亚尔正式命名为汝拉纪。至于“侏罗纪”的译法,则来自日语的汉字音读。其它如奥陶纪、志留纪等译名,也都是如此。这些译名早已约定俗成,看不到重新修订的迹象。
二,
“世界最大的恐龙”展,设在一个特别布置的展览空间。你会感觉一头撞进《纳尼亚》里的魔法壁橱,然后在另一个世界走迷了路。
周边是遮天蔽日的中生代密林。你恍惚觉得半空中有两只眼睛,猛一抬头,还以为枝叶间探出一条巨蟒。定睛再看,原来那是一座蜥足类恐龙模型的长脖子。这是银龙,科学已知最大的恐龙,仅在阿根廷发现过高度残损的化石。当它在白垩纪的贡瓦纳大陆兴盛繁衍时,我们更为熟悉的蜥足类,如梁龙、迷惑龙、圆顶龙和腕龙,早已在侏罗纪晚期,北方的劳亚大陆上灭绝了。

点题之后,你被引入一段曲折的走廊,走过人工布置的古植物丛林。低调的照明,营造出牧歌般的天地,甚至带有温室效果——一个史前世界被换算成气氛祥和的室内场景。展览完全排除了这类叙事中常见的,赤牙红爪的血腥厮杀。这里要讲的重点,只是动物的体量。虽然体量也是一种生存竞争的策略。低头再看脚下,就会看见印在地板上的恐龙脚印。估计得穿两百多号的鞋吧?再看步幅,几乎要用丈量。
布展人告诉我们,块头大小不仅仅是个外表问题。个头大,吃得就多,活得也长;反之就要通过频繁而大量的繁殖,增加种群延续的机会。但这里有个限度。大的同时也意味着重,这就需要消耗更多能量,支撑和移动沉重的身体。蚂蚁可以举起百倍于自重的物体。相比之下,奥运会举重记录简直算不了什么。四百多年前,伽利略就曾观察到:一只小狗能背起三只和它一样大的狗,而一匹马就未必驮得动另一匹马。
这里关注的不光是恐龙本身,还有它们所在的生态环境。这种系统性看待问题的眼光,近年在各个领域都很时兴,比如学者写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传,最后的书名通常叫做“某某和他的世界”。
于是展品中就少不了植物和史前昆虫的模型。其中一只古蜻蜓的长度和翼展,和现在小孩玩的模型飞机差不多。有人把这归结于古大气中更高的含氧量。但在大型恐龙生活的侏罗纪和白垩纪,大气中的氧气比重虽然高于今天,但并不特别显著。
自然选择才是更好的解释。任何物种在其历史早期,体量都很迷你,然后逐渐壮大。在生存和求偶竞争中,个头大的容易取胜,基因被保存复制的机会更多。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,就是别人轻易不敢惹你。就算一群狮子,要打成年犀牛或是大象的主意,也得好好掂量掂量。结果就会出现一些大到不能倒的霸主们。它们占尽优势,直到固有生态系统全面崩溃,历史翻至新的一页。
占据展厅中心位置的,是一具全尺寸的马门溪龙模型。这个模型的右侧,模拟恐龙的完整外貌;左面则是剥皮露骨的解剖图样。你可以看到皮下的肌肉、动脉、静脉、椎骨、食道、气管。同时它的这一侧面,还被设计成投影录像的屏幕:动态的录像画面,展示出远古动物的内脏如何运作。
这是来自中国的蜥足类恐龙,首次发现于1952年,在四川宜宾的马鸣溪渡口。由于地处公路建筑工地,于是起了个“建设马门溪龙“的学名。这个命名多少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。至于马鸣溪如何成了马门溪,据说造成错误的原因,是研究人员的口音问题。看来讲好普通话确实重要。

严格说来,马门溪龙算不上最大的恐龙。但它有一点特别,即按比例算,它的脖子最长,占到身长的一半。即便以蜥足类的标准衡量,这个比例也很夸张。而脖子的长度,恰好是这次展览的主要话题。参与策展的另一位科学家,波恩大学教授马丁·桑德尔,提出了一个外行人听来十分怪异的观点。他领导着一个分工细密的团队,包括营养学、工程学、生物力学、古植物学,等不同领域的专家,共同研究蜥足类恐龙体型庞大,颈部超长的原因。
桑德尔认为答案在于这类恐龙进食的方式:它们囫囵吞咽,而不是咀嚼嘴里的食物。他说咀嚼虽有助于消化,却延长了进食过程。展厅一角,安置着一个透明容器,里面装满蕨类、木贼等植物的枝叶,分量超过半吨。那是马门溪龙每天的食量。如果像大象那样细嚼慢咽,则要花上30小时才能吃完那份“绿沙拉”。然而一天只有24小时,即便省去睡眠时间。
但这需要更加复杂的消化过程,或通过胃石研磨(像鸡那样),或依靠发酵。投影在马门溪龙躯干上的录像,呈现了这个过程。吞咽有个好处,就是不需要强大的嚼肌,从而允许头部长得更小、更轻,随着细长的脖子,上下左右灵活地移动;几十吨重的躯体原地不动,也能够到高处和远处的植物嫩叶。CT扫描表明,蜥足类恐龙像鸟类一样,骨骼内有空腔,所以结构相对更轻。
然而头小,颅腔就小,脑容量自然不会很大。那这些恐龙的脑子够用吗?诺雷尔说,虽然它们不是思想家,但也不傻,否则不可能在地球上游荡一亿多年。一般来说,素食动物没有肉食动物聪明,毕竟它们的食物不会反抗,也不会逃跑。
展览看到这里,我们可以这样总结:古脊椎动物学这个词里,虽然还有脊椎二字,但这门学问早已不再限于和骨头打交道。它更关心动物的软组织,以及它们的行为方式。说起来,这也不是什么新潮流。科学家对这类问题的思考,已经进行了不少年,甚至在大众文化中,也有所反映。
三,
这件事说起来,也快有20年了。当时斯皮尔伯格正在夏威夷,拍摄根据同名畅销书改编的科幻惊悚片《侏罗纪公园》。他请到几位古脊椎动物学界的大腕级人物,充当剧组的科学顾问。其中有个叫约翰·霍纳的,据说就是克莱顿的小说中,那位男主角的人物原型。
一次,拍摄进行到一场重头戏,千钧一发的那种:故事里的两个小孩,被一群凶猛的速盗龙,围堵在一间冷藏库里。其中一只,隔着玻璃窗朝里张望,分叉的舌头,咝咝地吞吐着。霍纳一看,说这不对。速盗龙这样的肉食恐龙,是代谢水平很高的恒温动物,不是冷血爬虫,怎么会吐出蛇信子似的舌头?于是建议修改。剧组人员灵机一动,设计出一个极富想象力的镜头,他们让速盗龙在冷藏室冰凉的窗玻璃上,呼出一片雾蒙蒙的哈气。体温的感觉就这样烘托出来了。
高成本大片的投资,很多是用在这类细节上。但这背后的知识储备,却是一种很难用“新钱”直接兑换的资本。而且你越是爱问这有什么用,积累起来就越难。文革期间有个电影里,葛优他爸在课上讲马尾巴的功能,这种无用的知识,遭到革命学生的叱笑。很多东西,就是这样给笑没的。
回到前面的话题。霍纳的说法,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古生物学家的新看法。在同行中间,他是个印第安纳·琼斯式的的人物,曾经挖掘到八具珍贵的霸王龙化石。但他最重要的贡献,却是通过研究新发现的慈母龙(一种鸭嘴龙),确认某些恐龙具有类似鸟类的行为特征,比如筑巢和育雏。
上世纪60年代,那个造反有理的年月,就像从文化到科技的所有领域,古生物学界也发生过一场小规模革命,被称做“恐龙复兴”。激进的科学家推翻了一些陈旧的学说,比如把恐龙描绘成蠢笨的,在生存竞争中淘汰的物种。他们认为至少部分恐龙是恒温动物,而且是鸟类的祖先,有复杂的社会行为。《侏罗纪公园》里的速盗龙发动攻击时,那种全攻全守式的战术配合,就是这种观点的图解。
当文科理论家的眼光,从孤立的文本细读转移到语境研究,古脊椎动物学也不再限于化石的分析和描述。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,他们谈论研究领域中那些“软”的,甚至“虚”的部分,像恐龙的社会行为、生理功能以及它们生活的世界——它们是什么颜色?长不长毛?昼行还是夜行?能跑多快?——就像我们在“世界最大的恐龙”,这个展览中看到的那样。
人们对恐龙的兴趣,不仅在于其兴,也在于其亡。以前有个主流说法:这些呆滞的巨兽在生存竞争中,败给了聪明灵活的哺乳动物。卡尔维诺在小说《宇宙连环画》里,写过一头大灭绝后幸存的恐龙,混入一群新兴的哺乳动物,成了饱受冷眼的怪物和受气包。那些历史的宠儿,年复一年地重复一个反恐龙战斗故事,好像他们从来就是战无不胜的优良物种。
1980年,美国地质学家阿尔瓦雷兹在意大利野外勘察。他在峭壁间发现一处岩层,地质年代处于六千五百万年前的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。当时发生过一次物种大灭绝,兴盛的恐龙王朝,就在那时骤然毁灭。
阿尔瓦雷兹发现岩层中的金属铱含量,明显超过地表平均值。很快世界各地都发现该地层铱含量超标。这种元素在地壳中含量稀少,大多来自地幔,以及陨落地面的陨石和彗星等。他假设六千五百万年前,一个巨大的外来星体曾撞击地球。飞来横祸引发毁灭性地震、飓风、海啸,以及全球性火灾。全球生物减员过半,并由此重新洗牌。
恐龙的退出,为哺乳动物的发展,带来亿载难逢的机会。这个弱小种群,被长期排挤在生存舞台边缘,从未显示出竞争优势。它们捕食昆虫和软体动物,而后者依赖土壤中的腐殖质就能存活。寒酸的食谱让那些毛茸茸的惊慌小兽,在危难中觅得一线生机。这次生物史上意义重大的兴亡更替中,起决定作用的是天意,而非强者胜出的达尔文主义逻辑。
那么恐龙真的早已全部死光?并不是完全是这样。它们的后裔至今在世界上跃行,飞翔。越来越多的古生物学家相信,鸟类是兽足类恐龙的遗族。它们是6千5百万年前那场大灭绝的的幸存者。不论19世纪发现于巴伐利亚的始祖鸟标本,还是近年来自中国辽西的孔子鸟和带羽毛的兽足类化石,都说明恐龙到现代鸟类之间,存在着进化链的众多环节。
四,
“世界最大的恐龙”的一个有趣布置,是它的互动部分。你可以触摸一些化石,体会它们的质地和分量。这里有一间展室,沙盘里面随处凸现出一些化石复制品。你可以用博物馆提供的工具,体会野外挖掘作业。跑到这里动手的,主要是些孩子。他们的父母正在隔壁大厅,专注于更复杂的古生物学问题。这种安排让我想到麦当劳的儿童游艺区。做为成人,你也可以过去体验一番,临时把自己当成专家,玩一会儿科学探险卡拉OK。

其实在国内,有个地方可以在更大范围内,体会古生物学的田野作业。几年前,德国古生物学家布尔克哈德·珀尔在辽西锦州附近的益州县,和当地合作建成了辽宁化石地质公园。这里除了正常的化石收藏、展示,另外开设了一处蒙古包营地。这里每年接待的人数不超过两千,除了部分游人,还有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科学家。观众、游客和古生物学家的角色,在这里是相互开放的。
博物馆和化石园区的总经理达米昂·勒鲁认为,科研活动应该面向所有人群,让他们有机会在一个侏罗纪公园式的背景下,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。他同时强调,必须限制来访者的批次和数量。人数一多,服务质量就会降低,高水平的交流更是空谈。受季节和环境限制,园区只在每年4到10月间开放。国内游人一般只是短时间参观,而参加化石采集研究的,仍然是外国人居多。

这个年轻的法国人以前从事潜水,参加过海洋探险名家雅克·古斯图的团队。由于他对古生物学的兴趣,还有艺术方面的专长,被请去打理化石公园和博物馆的日常事务。他强调恐龙不是一堆落满灰土的石头,它们本来是活的,要让人感觉到这一点。
再就是环保。博物馆使用的电力,主要来自风力和太阳能,还要实行全面的回收政策。勒鲁说:“当我离开的时候,这里要比我当初来的时候好,而不是相反。”他说服老板,要让这块不毛之地恢复生机。他们开掘出一片人工湖,然后种植了五千棵树。很快便有26种鸟类前来筑巢,还有大量的昆虫和若干种爬行动物,然后是刺猬。
近十几年,辽西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古鸟类,以及似鸟兽足类恐龙化石。这些发现为鸟类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假说,提供了重要佐证。但有一件事让我好奇,那就是中国的科学家,似乎很少提出理论上的这类假说。他们好像从不热衷讲述自己的“大故事”。对此我请教过几个有名的专家,然而他们却对我的好奇心,报以一致的沉默。或许我的问题实在太愚蠢。
0
推荐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